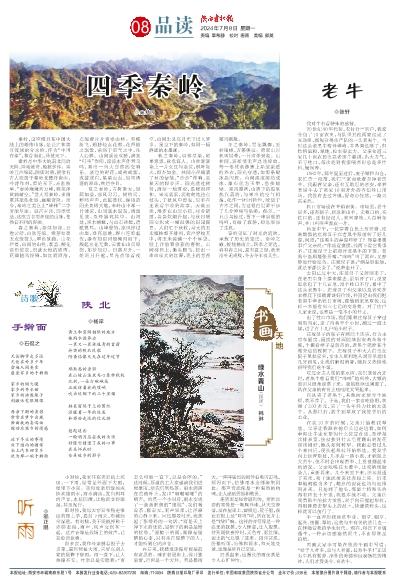发布日期:
2024年07月08日
老牛
张轩
我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分产到户,我家分包了10亩农田,与队里其他两家组成了互助组,抓阄分得生产队的一头老黑牛。当时这头老黑牛瘦骨嶙峋,牛鼻圈也断了,但性情温和,犁地、拉车很卖力。父亲知道三家几十亩农田全靠老黑牛翻耕,出大力气,不亏牲口,每次轮到我家喂养时总是多拌料、勤饲养。
1982年,那年夏至过后,麦子颗粒归仓,农忙告一段落,我们三家商量着卖掉老黑牛。我跟着父亲,还有互助组的老安,牵着老黑牛去了离家10里开外的齐镇牲口市场。我没有去过齐镇,好奇心使然,一路兴高采烈。
牲口市场设在齐镇南街。市场里,耕牛居多,还有骡子、猪崽和山羊。卖牲口的、买牲口的,还有经纪人,来回穿梭,人员嘈杂声、牲口叫唤声混成一片。
临近中午,一位穿着白色土布汗褂、皮肤黝黑的庄稼汉子在老黑牛跟前转了好几圈,问道:“这黑牛的鼻圈咋断了?得是很费事?”父亲说:“你凑近摸摸,拽两下看它费事不。”庄稼汉子上前掰开老黑牛的下颚。老黑牛温顺地张开嘴,“哞哞”叫了两声,又静静地开始反刍。庄稼汉子说:“倒是很温顺,就是牙都长全了。”说着走开了。
太阳已过中天,庄稼汉子又转回来了,在老黑牛身上摸来摸去,最后开了口,说家里承包了十几亩地,没个牲口不行,相中了这头老黑牛。庄稼汉子和父亲以及老安在衣襟底下捏揣着谈好价钱,并商定由我们把老黑牛牵出牲口市场,跟他到家里取钱,这样一来能省出六七元的交易费。对于庄户人家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出了牲口市场,我们跟着庄稼汉子穿过南街向东,走了约莫半个小时,翻过一道土墚,进了有十几户的小村子。
庄稼汉子的院子有两间土坯房,分为主房和厢房,厢房的对面院墙跟有鸡舍和牛棚,牛棚看样子是新盖的,老黑牛就拴在牛棚旁边的槐树下。庄稼汉子和大人们坐在院子里拉家常,女主人麻利地从厨房里端出几牙西瓜,让我们解渴消暑,随后又热情地招呼我们吃午饭。
吃过女主人做的浆水面,我们准备离开时,老黑牛朝着我们“哞哞”地叫唤,大颗的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我的眼眶也潮湿了,趴在父亲的脊背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自从卖了老黑牛,其他两家嫌养牛麻烦,就不养了。于是,我们一家省吃俭用,积攒了500多元,买了一头年轻力壮的大黄牛。从那以后,放牛割草成了我放学后的主业。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犁地。父亲让我跟在他后头边走边看,如何牵绳让牛走在犁沟什么位置合适,犁铧每次排多宽,扶杖扶到什么角度翻出的泥花深浅刚好,地头如何转犁。我跟着看过几个来回后,便扶起犁杖开始犁地。我双手向上扶着犁杖,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大黄牛,但不时会出现滑犁、土没被翻起来的情况。父亲吆喝住大黄牛,让我稍微歇会儿,重新再来。几个来回下来,汗水湿透了夹袄,我干脆脱掉夹袄赤膊上阵。后来犁地就稳当多了,翻出的泥花也均匀地排列开来。只是到了地头,那湿土将犁头沾得有四五十斤重,我根本拽不动。父亲让我借助牛的拉力惯性,双手向后提起犁杖,再用脚蹬去犁头上的泥土,快速调转头,这样就可以前行了。
牛一直养到我师范毕业。割草、铡草、起粪、垫圈、犁地,这些与牛有关的活儿也一直伴随着我的学生时代。现在,每次下乡偶遇牛,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不由得驻足拍照。
国画大家李可染在他的牛画中写道:“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正因为牛具有勤劳、淳朴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人们才赞美牛、喜欢牛。
我对牛有着特殊的感情。
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分产到户,我家分包了10亩农田,与队里其他两家组成了互助组,抓阄分得生产队的一头老黑牛。当时这头老黑牛瘦骨嶙峋,牛鼻圈也断了,但性情温和,犁地、拉车很卖力。父亲知道三家几十亩农田全靠老黑牛翻耕,出大力气,不亏牲口,每次轮到我家喂养时总是多拌料、勤饲养。
1982年,那年夏至过后,麦子颗粒归仓,农忙告一段落,我们三家商量着卖掉老黑牛。我跟着父亲,还有互助组的老安,牵着老黑牛去了离家10里开外的齐镇牲口市场。我没有去过齐镇,好奇心使然,一路兴高采烈。
牲口市场设在齐镇南街。市场里,耕牛居多,还有骡子、猪崽和山羊。卖牲口的、买牲口的,还有经纪人,来回穿梭,人员嘈杂声、牲口叫唤声混成一片。
临近中午,一位穿着白色土布汗褂、皮肤黝黑的庄稼汉子在老黑牛跟前转了好几圈,问道:“这黑牛的鼻圈咋断了?得是很费事?”父亲说:“你凑近摸摸,拽两下看它费事不。”庄稼汉子上前掰开老黑牛的下颚。老黑牛温顺地张开嘴,“哞哞”叫了两声,又静静地开始反刍。庄稼汉子说:“倒是很温顺,就是牙都长全了。”说着走开了。
太阳已过中天,庄稼汉子又转回来了,在老黑牛身上摸来摸去,最后开了口,说家里承包了十几亩地,没个牲口不行,相中了这头老黑牛。庄稼汉子和父亲以及老安在衣襟底下捏揣着谈好价钱,并商定由我们把老黑牛牵出牲口市场,跟他到家里取钱,这样一来能省出六七元的交易费。对于庄户人家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出了牲口市场,我们跟着庄稼汉子穿过南街向东,走了约莫半个小时,翻过一道土墚,进了有十几户的小村子。
庄稼汉子的院子有两间土坯房,分为主房和厢房,厢房的对面院墙跟有鸡舍和牛棚,牛棚看样子是新盖的,老黑牛就拴在牛棚旁边的槐树下。庄稼汉子和大人们坐在院子里拉家常,女主人麻利地从厨房里端出几牙西瓜,让我们解渴消暑,随后又热情地招呼我们吃午饭。
吃过女主人做的浆水面,我们准备离开时,老黑牛朝着我们“哞哞”地叫唤,大颗的眼泪从眼角滚落下来。我的眼眶也潮湿了,趴在父亲的脊背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自从卖了老黑牛,其他两家嫌养牛麻烦,就不养了。于是,我们一家省吃俭用,积攒了500多元,买了一头年轻力壮的大黄牛。从那以后,放牛割草成了我放学后的主业。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开始教我犁地。父亲让我跟在他后头边走边看,如何牵绳让牛走在犁沟什么位置合适,犁铧每次排多宽,扶杖扶到什么角度翻出的泥花深浅刚好,地头如何转犁。我跟着看过几个来回后,便扶起犁杖开始犁地。我双手向上扶着犁杖,几乎是一路小跑,才能跟上大黄牛,但不时会出现滑犁、土没被翻起来的情况。父亲吆喝住大黄牛,让我稍微歇会儿,重新再来。几个来回下来,汗水湿透了夹袄,我干脆脱掉夹袄赤膊上阵。后来犁地就稳当多了,翻出的泥花也均匀地排列开来。只是到了地头,那湿土将犁头沾得有四五十斤重,我根本拽不动。父亲让我借助牛的拉力惯性,双手向后提起犁杖,再用脚蹬去犁头上的泥土,快速调转头,这样就可以前行了。
牛一直养到我师范毕业。割草、铡草、起粪、垫圈、犁地,这些与牛有关的活儿也一直伴随着我的学生时代。现在,每次下乡偶遇牛,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不由得驻足拍照。
国画大家李可染在他的牛画中写道:“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正因为牛具有勤劳、淳朴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人们才赞美牛、喜欢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