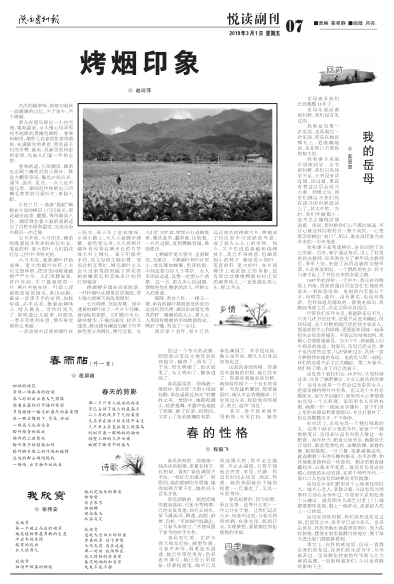日期检索:
烤烟印象


赵玲萍
淡淡的烟草味,每每勾起我一段暖暖的记忆,关于家乡,关于烤烟。
男人在屋后辟出一小块空地,建起温室,女人精心侍弄那些不起眼的黑褐色烟籽。春寒料峭里,烟芽儿在春的张望里萌发,充满新生的希望,那是孩子们的学费、新衣,是新居里待添的家具,是农人们新一年的念想。
春寒渐退,小苗圃里,烟苗生出两三瓣机灵的小圆叶。移进大棚营养居,像是沙场点兵,通风、浇水、见光,一点儿也不能马虎。烟苗很快伸展出三四瓣毛茸茸的可爱叶片,青碧入眼。
乡村三月,一条条“银蛇”蜿蜒在乡间的梯田上闪闪发光,那是烟田起垄、覆膜,等待烟苗入住。烟苗耷拉着小脑袋逐渐适应了自然光照和温度,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迁徙。
五月多雨,六月阳光,烟苗吮吸着雨水和养料疯狂生长。笔直的秆,宽大的叶,人们掐花打岔,让叶片养料充裕。
八月未央,底部烟叶开始成熟。宽大的烟叶在秆上左右交替伸展,把田垄间隙遮蔽得严严实实。人们弯腰匍匐,穿行其间,采下最底部的一片、两片夹抱在怀。叶面上浮着细密密的绒毛,渗出油脂,凝成一层黑乎乎的东西,如胶似漆,沾手沾衣,散着油烟味儿,呛人鼻息。劳作时间久了,那味道让人眩晕,但眼见一季辛劳胜利在望,便不再觉得那么难耐。
一沓沓绿中泛黄的烟叶在三轮车、架子车上垒成堆垛。乡间小路上,大人小孩脚步铿锵。按色度分类,大人将两片烟叶背对背在两米长的竹竿或木杆上绑扎。孩子们眼疾手快,是父母的左膀右臂。邻居总相互帮忙,绑完烟叶主人会从自家菜园里摘下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和美味多汁的西红柿犒赏。
烤烟楼多建在自家院落。一杆杆烟叶在楼里层层架起,草木柴火烧两天再改用煤炭。
七天烧烤,犹如涅槃。绿中透黄的烟叶成了一片片干花瓣,黄灿灿的惹眼。它们散尽水分,凝结精华,干瘪而凌厉,轻灵又透亮,移出楼待潮湿后解下竹竿按色度分类绑扎,便可交售。女人们忙完伙食,便埋头扎进烟堆里,像是选秀,翻弄着,比较着,一片片过眼,直到腰酸背痛,鼻呛眼花。
上乘烟叶宽大厚实、金黄鲜亮,无斑点。下乘烟叶则叶片窄小,或是薄如蝉翼,色泽枯暗,中间还要分好几个等次。女人多深谙此道,良莠一定要分个清楚。这一点,男人多心悦诚服,便做些包扎整装的活儿,听候女人的差遣。
霜降,肃杀入秋。一楼又一楼,所有的烟叶都脱离母体经历这场炽烈炙烤,烟田里徒留光秃秃的秆。暖暖的炕头上,男人女人用同样粗糙的手细数着收成,咧开了嘴,笑成了一朵花。
离开家十余年,家乡已是远近闻名的烤烟大乡,烤烟成了村庄里不可或缺的风景,成了农人心头上的牵绊。如今,关于先进的栽植和烧烤技术,我已不再熟悉,但烟草细小的种子、萌发的小圆叶、笔直的秆、宽大的叶,在乡间梯田上威武挺立的身影,还有那丝丝缕缕飘散在村庄里的烟草味儿,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