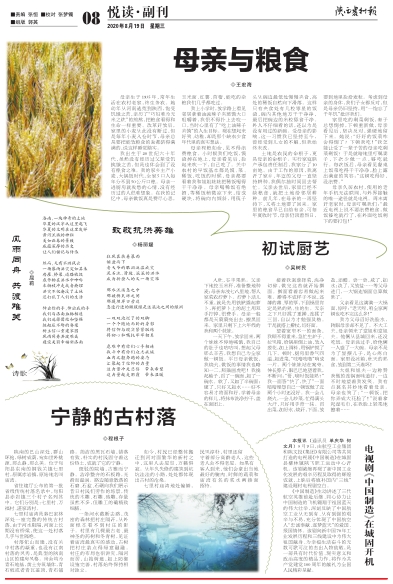日期检索:
母亲与粮食


王宏海
母亲生于1935年,常年生活在农村老家,终生务农。她幼年从河南逃荒到陕西,饱受饥饿之苦,亲历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煎熬,把粮食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改革开放后,家里的小麦从此没有断过,但是每年小麦入仓时节,母亲总是要把能放粮食的瓮都装得满满的,说这样睡觉踏实。
我出生于20世纪六十年代,虽然没有经历过父辈受饥挨饿之苦,但是也体会到了没有粮食之难。我的家乡主产小麦,大锅饭时代,全家5口人每年分不到50公斤口粮。母亲一进厨房就发愁的心情,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做饭真是费尽心思,玉米面、红薯、苜蓿,能吃的杂粮我们几乎都吃过。
我上小学时,放学路上看见邻居拿着油泼辣子夹蒸馍大口咀嚼着,我恨不得扑上去咬一口,当时心里有了“吃上油辣子夹馍”的人生目标。现在想起来好笑、幼稚,却是那个缺衣少食年代里的真实想法。
母亲视粮如命,见不得浪费粮食。小时候我们吃饭,馍渣掉在地上,母亲看见后,捡起来吹一下,自己吃了。关中农村的早饭基本都是馍、菜、稀饭,吃饭的时候,母亲都要看着我和姐姐妹妹把稀饭喝得干干净净。母亲喝稀饭有绝招,等稀饭稍微凉下来,结成硬块,将碗向内倾斜,用筷子头从碗边最低处慢慢夹食,高处的稀饭自然向下滑落。这样只有夹食处有几粒零星的饭渣,碗内其他地方干干净净,最后把碗边的米粒舔食干净。外人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没有用过的新碗。受母亲的影响,这一习惯我已坚持至今,曾经受到儿女的不解,但我始终未改。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更是母亲的命根子。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家分了10亩地。由于工作的原因,我离开了家乡,年迈的父母一直坚持耕种,我偶尔抽时间回去帮忙。父亲去世后,家里已经不缺粮食,就把土地给邻居耕种。前几年,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又将土地要了回来。家里的粮食早已自给有余,可每年夏收时节,母亲仍顶着烈日,要到地里捡拾麦粒。考虑到母亲的身体,我们子女都反对,但是母亲仍旧坚持,用“一饱忘了千年饥”批评我们。
家里吃的剩菜剩饭,妻子总想倒掉,下顿重新做,母亲看见后,坚决反对,强硬地留下来。她说:“好好的饭菜咋舍得倒了?下顿我吃!”我怎能让受了一辈子苦的母亲吃剩菜剩饭?于是就暗地里叮嘱妻子,下次少做一点,够吃就行。每次饭后,母亲看见餐桌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这顿吃得好,没浪费。”
母亲久居农村,使用的老年手机无法联网,与外界接触的唯一途径就是电视。周末离开老家时,母亲叮嘱我们:“最近电视上说不要浪费粮食,做饭够吃就行了,在外面吃饭剩下的要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