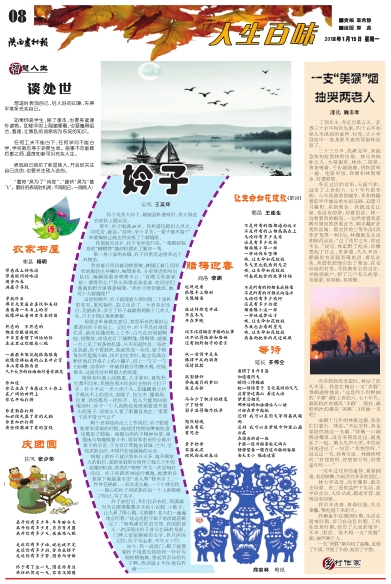日期检索:
妗子
宝鸡 王英辉
妗子是我大妗子,她嫁到外婆家时,我大舅还在部队上服兵役。
那年,妗子刚满20岁。我外婆见媳妇人灵光,肯吃苦,就说:“娃呀,学个手艺,一辈子饿不着!”外婆掏钱让她去西安报了个裁缝班。
我舅复员返乡,妗子也学成归来,一架簇新锃亮的“蝴蝶牌”缝纫机摆在了厦房一角。
第一身小孩的衣服,妗子自然是送给我这个外甥的。
我穿着后背印着动物图案,裤腿压着几何图形的服装出早操时,被樊乖英、令彩琴老师叫出队伍,她俩围着我啧啧不已:“在哪买的新袄袄?漂得很么!”我头扬得老高老高,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里得意喊着:“我妗子给我做的,她是个大裁缝哩!”
没轻松两年,妗子就随着大舅回到二十里外的老宅,重起锅灶,独立生活了。大表弟出生后,花销渐多,多亏了妗子裁裁剪剪换个几块几毛,日子才得以艰难掀磨。
舅舅去外地做生意后,家里所有的重担全都落在妗子的肩上。记忆中,妗子不是在地里忙活,就是在缝纫机上工作,白天在田间刨啊刨,挖啊挖,夜里在灯下缝啊缝,绣啊绣,就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从不知道休息。每次走亲戚,妗子看到我,脸就笑成一朵花,屋子犄角旮旯踅摸半晌,找不出吃货时,她总是满含歉疚地打开桌子上的小罐子,舀上一勺又一勺白砂糖,给我冲一杯浓得黏牙的糖水喝,在她看来,这就是对外甥最大的疼爱。
舅舅有时遇上活路重,人手紧时,夏收秋忙都不回来,我便在周末休息时去给妗子打下手。妗子不足一米六的个头,却蕴藏着小伙子都比不上的劲头,割麦子、挖玉米、摞柴垛、拉粪、扬场都是一把好手。别人天擦黑回家喝汤时,妗子一个人还跪在地里割着望不到头的麦子,邻家女人看了眼圈直发红:“素素干活不惜力气么!”
两个表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妗子眼看着要享清福的时候,她却因持续咳嗽被检查出罹患了肺癌。病倒后的妗子精神如常,顽强地与病魔做着斗争,舅舅和表弟怜念她半辈子的辛苦,千方百计带她去省城、兰州、宝鸡求医治疗,不惜代价延缓她的生命。
病榻上的妗子意识到来日无多,她不顾家人的阻拦,重新坐到那台陪伴了她几十年的老缝纫机前,熟悉的“嗒嗒”声又一次回响在房间。妗子在跟死神进行赛跑,她要给孙辈留下她最拿手的“亲人牌”精美手工,一件件花棉袄,一双双虎头鞋,一个个绣花枕……细心的妗子用纸条在每一个上面都做了标记,写了名字。
妗子辞世后,我们拉开衣柜,那满满当当且摆得整整齐齐的小衣服、小鞋子,让人看了既心酸,又震撼!老人们一遍遍地念叨着:“娃这是把今辈子的活提前做完了。”唢呐凄厉的哀号里,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妗子昔日忙碌的身影,门牌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我只深深记住:妗子吴金素,卒年五十四。
如今,我一进家门,脚下就摆着妗子用蓝毛线给我一针针勾制的棉拖鞋,想起我苦命的妗子啊,热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
妗子是我大妗子,她嫁到外婆家时,我大舅还在部队上服兵役。
那年,妗子刚满20岁。我外婆见媳妇人灵光,肯吃苦,就说:“娃呀,学个手艺,一辈子饿不着!”外婆掏钱让她去西安报了个裁缝班。
我舅复员返乡,妗子也学成归来,一架簇新锃亮的“蝴蝶牌”缝纫机摆在了厦房一角。
第一身小孩的衣服,妗子自然是送给我这个外甥的。
我穿着后背印着动物图案,裤腿压着几何图形的服装出早操时,被樊乖英、令彩琴老师叫出队伍,她俩围着我啧啧不已:“在哪买的新袄袄?漂得很么!”我头扬得老高老高,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里得意喊着:“我妗子给我做的,她是个大裁缝哩!”
没轻松两年,妗子就随着大舅回到二十里外的老宅,重起锅灶,独立生活了。大表弟出生后,花销渐多,多亏了妗子裁裁剪剪换个几块几毛,日子才得以艰难掀磨。
舅舅去外地做生意后,家里所有的重担全都落在妗子的肩上。记忆中,妗子不是在地里忙活,就是在缝纫机上工作,白天在田间刨啊刨,挖啊挖,夜里在灯下缝啊缝,绣啊绣,就像一台上足了发条的机器,从不知道休息。每次走亲戚,妗子看到我,脸就笑成一朵花,屋子犄角旮旯踅摸半晌,找不出吃货时,她总是满含歉疚地打开桌子上的小罐子,舀上一勺又一勺白砂糖,给我冲一杯浓得黏牙的糖水喝,在她看来,这就是对外甥最大的疼爱。
舅舅有时遇上活路重,人手紧时,夏收秋忙都不回来,我便在周末休息时去给妗子打下手。妗子不足一米六的个头,却蕴藏着小伙子都比不上的劲头,割麦子、挖玉米、摞柴垛、拉粪、扬场都是一把好手。别人天擦黑回家喝汤时,妗子一个人还跪在地里割着望不到头的麦子,邻家女人看了眼圈直发红:“素素干活不惜力气么!”
两个表弟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妗子眼看着要享清福的时候,她却因持续咳嗽被检查出罹患了肺癌。病倒后的妗子精神如常,顽强地与病魔做着斗争,舅舅和表弟怜念她半辈子的辛苦,千方百计带她去省城、兰州、宝鸡求医治疗,不惜代价延缓她的生命。
病榻上的妗子意识到来日无多,她不顾家人的阻拦,重新坐到那台陪伴了她几十年的老缝纫机前,熟悉的“嗒嗒”声又一次回响在房间。妗子在跟死神进行赛跑,她要给孙辈留下她最拿手的“亲人牌”精美手工,一件件花棉袄,一双双虎头鞋,一个个绣花枕……细心的妗子用纸条在每一个上面都做了标记,写了名字。
妗子辞世后,我们拉开衣柜,那满满当当且摆得整整齐齐的小衣服、小鞋子,让人看了既心酸,又震撼!老人们一遍遍地念叨着:“娃这是把今辈子的活提前做完了。”唢呐凄厉的哀号里,我的眼前又一次浮现出妗子昔日忙碌的身影,门牌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我只深深记住:妗子吴金素,卒年五十四。
如今,我一进家门,脚下就摆着妗子用蓝毛线给我一针针勾制的棉拖鞋,想起我苦命的妗子啊,热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